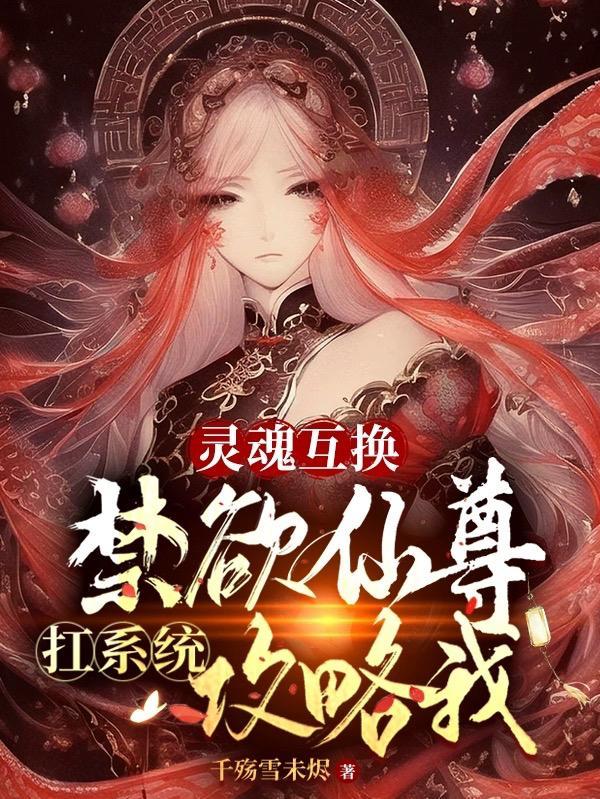大文学>金玉满堂 > 第251章(第1页)
第251章(第1页)
“你别紧张,我姆妈和小姑你又不是没见过。”沈满棠在桌下偷偷握住金朝的手,和他耳语道。
“我没紧张。”金朝话虽这么说着,腿却又不受控制地抖了起来。他敢说,哪怕在枪林弹雨里,他都没有像此刻这般惊心动魄过。
好在还有沈满棣这个活宝活跃气氛,挑挑拣拣地和金朝反馈哪款糖好吃,哪款糖还有待改进,总算是勾得金朝多说了几句话。
一餐饭就这么其乐融融地过去了,大家虽没有明说,但也都彼此默认,从此金朝便作为沈满棠的伴侣,成为沈家的一份子了。芦荟看着大家很给面子地吃完了她准备了一天的饭菜,为金朝捏了把汗的心才总算是放下了,这才后知后觉地吃出了饭菜的味道。
金朝本以为这场算不上是考验的会面已经结束了,可没想到沈攸却意外地在饭后叫住了他。“元宝,我能单独和你说会儿话吗?”
金朝定在原地,僵硬地点了点头,跟随沈攸去了书房。比起被他拐了儿子的傅君佩,他更不敢面对的,其实是因他才失了母亲和爱人的沈攸。
“四小姐。”金朝站在沈攸面前,明明比她高出了一大截,却像是犯了错的孩子,把头埋到了衣领里。
“别这么见外,你既然和小满在一块了,就随他叫我一声‘姑姑’吧。”沈攸指了指沙发,示意他坐下,“我喊你来,其实是为了陶园昌的事。”
二月的天,金朝却出了一身冷汗,把他的里衣都浸湿了。
“我也是后来从小满口中得知,是你和他一起创办了福臻。我想你们的关系一定非常好,所以才冒昧地请你来同我聊聊。”
“好,四小姐想知道什么,我一定知无不言。”
“园昌以前同我提过,他身边有一位很厉害的小友,为他出了许多生意点子,还独自一人去爪哇闯出了一片天来。我想,这位小友应该就是你。只可惜我从前对他很是不好,从来不耐烦听他讲话,不然今日我也能与你分享许多他的独家秘事了。”沈攸仰头靠在沙发上,眼睛茫然地瞟着,却无能为力地发现,自己真的再想不出更多陶园昌对她说过的话了。
“我很后悔,他活着时我为什么不对他好一点,非要等他死了才摆出这副惺惺作态的样子,做给谁看呢?”沈攸将手覆在眼皮上,似是终于找到了出口,将这半年多来积压的情绪统统宣泄了出来。
“我从来不信这世上有什么劳什子爱情。你看我爸妈、我大哥和三哥、还有我兄嫂,为了点朝更夕改的爱情把自己搞得死去活来,把家弄得支离破碎,值得吗?所以我从小就想着,我不需要爱人,我也不会爱上任何人,我只需要借结婚这个由头,帮我逃离这个家不像家的地方,哪怕这么做的代价是往后余生我都将和某个人不咸不淡地度过,但这也好过爱上一个人后把自己折磨到发疯。”
“可等我多次病急乱投医后才发现,原来婚姻并不是女子的第二次投胎,”沈攸指了指自己的太阳穴,“这儿觉醒才是。
“所以我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我嗤笑鄙夷所有对恋爱和婚姻还抱有幻想的蠢货,并对向我示爱的人展现我能表达的、最极端的恶意,哪怕他们什么都没做错。也就是在我最扭曲的时候,陶园昌出现了。他像是听不懂人话一样,每天傻呵呵地出现在我身边,嬉皮笑脸的真让人讨厌。有时还占用我们的热线电话,只为跟我说今日黄历上写不宜出行,叫我不要外出采风。你说他可不可笑?”
“直到我负责了一篇他的个人报道,才算是对这个人有所改观。但多可笑啊,他越是好,我却越是不敢要了。我这样一块永远捂不热的石头,哪里回馈的了他的期待。他这样至诚至善之人,该当有更好的女子爱他。”
“他死后,我一直在后悔,不是后悔没能和他在一起过,我只是后悔为什么非要口出恶言来贬低他的感情,让他至死都以为是自己还不够好,才没能打动我。”
“这话我没人能说,也说不出口,谢谢你还能坐在这里听我把话说完。你是他最亲近的兄弟,我这般辜负他,你就是恨我也是应该的。我欠他一句抱歉,今天也要对你说声抱歉。若是没遇到我,他最后的人生还能快活许多。”
沈攸说完,便真的站起身向金朝深鞠一躬,吓得金朝连忙将她扶起,又将内袋中常年为沈满棠备着的帕子扯出,塞给沈攸拭泪。
“四小姐,据我所知,陶哥遇上你后一直觉得很幸福,他前年还买了栋小洋楼,说是日后要当作你与他的婚房,就是现在我和沈满棠住的那栋!其实我早该把这房子还给你了,这是陶哥想着你才买的。你要想去看的话,我们现在就能出发。”
沈攸蒙着脸,微微摇了摇头:“不去了,我这样的人,不配去他的婚房。”
金朝有些着急,语气也变得冲了些:“四小姐,你今日同我说的话,陶哥泉下有知,也必定是笑着的。我了解他,他不是那般心胸狭隘之人,相反,他只会比任何人都更能理解你的苦衷。你若这般妄自菲薄,才当真是寒了他的心!他活着时都是一心为你,死了又怎会回过头来埋怨你?”
“你说你要跟我道歉……其实一直以来欠你一句道歉的人是我。没有我提前出现在他的生命里,又野心勃勃地跑去爪哇,最后还带着一艘船的货来让他押往关东,他就不会死。所以真正欠他的不是你,是我,是我害死的他!”金朝说到最后,音量已经接近于嘶吼,震得沈攸连泪都忘了流,怔怔地看着眼前这个年轻人从劝说她,到哭得比她还要崩溃难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