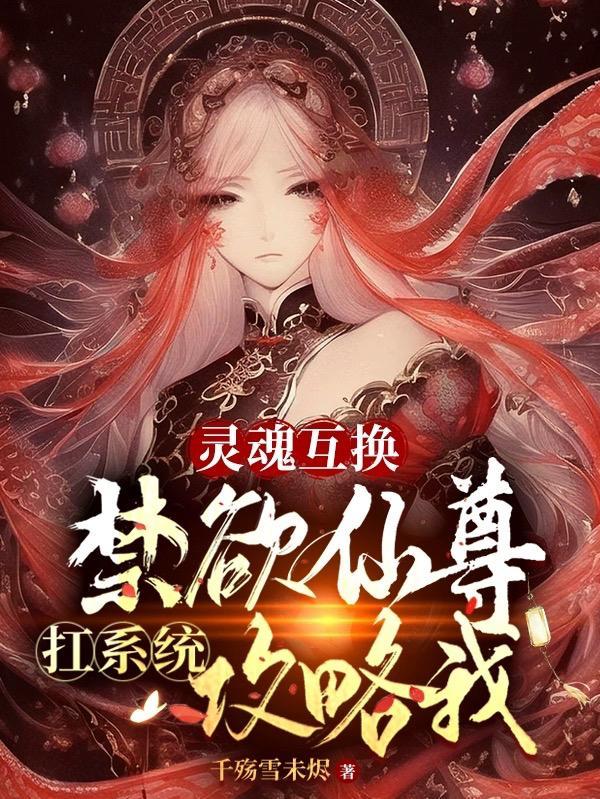大文学>当官不如食软饭 > 第143节(第1页)
第143节(第1页)
江寻鹤知晓为何董嬷嬷会说他母亲出嫁并不光彩,因为他母亲出身清流人家,原本身上压着婚约的,却同一商贾私通,最后不得已草草成亲。
这商贾便是江骞。
哪怕是在商贾平民之中,私通私奔也是要叫人耻笑的,所以江寻鹤这么多年来才会始终被那些人骂作孽种。
董嬷嬷似乎犹豫了很久,才小声道:“其实夫人当年并非是私奔,夫人同原定的郎君亦是青梅竹马,哪里会忽然私奔,这些都不过是场局罢了。”
她转身从床底下翻出了一个带锁的匣子,将里面的东西拿出来递给了江寻鹤:“这是夫人留下的书信,原本家主已经命人焚毁了,但我偷偷留下来了封。”
她也说不清自己当初为何会冒着风险将这信留下,要知道凭着江家心狠手辣的行事风格,一旦发现,只怕她便要难逃一死了。
这么多年她将这书信藏在床下,日日睡在上面,却是难有一日安眠。
可她又能有什么法子?她卖身契就在江家手中握着,她的儿子也在江家卖命,若是胆敢妄动,在这江岸淹死的人难道还在少数吗?
她能做的也无非就是这些,就当做是同为女子的最后一点怜惜吧。
书信已经泛黄,即便是被妥善地藏在木匣之中,也已经能看出岁月的痕迹。
江寻鹤手中握着那信,竟有种已经逾越千斤的感觉,他周遭的仆役纷纷不忍地撇开头去,这世上还有什么比自己想念多年的母亲却早已故去一事更叫人伤神?
江寻鹤最终还是将那信拆解开,可他没想到这信首竟写着:吾儿。
可若是说是写给江寻鹤的却又好像不尽然,更多的是一个逐渐走向绝望的女子写给自己、写给这世道的。
“他们曾无数次说过,一家之兴盛全在男子儿郎之身,因而这绢帛功名全捡着好的,一并贴在那堂堂郎君之身,好似这般便可流传千古,甚至将那棺椁之中的腐尸烂肉都熏香了般。”
“我不过是身为女儿身,便好似是背着什么劫难灾厄降生般,又要我贯学女工为家中充门面,又要我最好在这四方院子之中对一切男子做小伏低。便是个石头缝间的虫子,只要能分出雌雄,便胜败已见一般。”
“可到最后,那顶顶能干的儿郎个个畏首畏尾,撑不起门楣后,便干脆将我放到称上称了称份量,卖出个好价钱,好叫这一家都得以存活,最后也不过是落在那儿郎手中。”
“娘亲此生就错在徒有些刚烈的性子,却早已经在多年的教化之间软了骨头,倒最后白白地做了被男子踩在脚下的石头。我这一声恨透了女儿身,可若是来世,只愿我还能做得女儿身,彼时定不会同今世这般。”
“渡春江水寒,我捞不起旁人,也救不得自己。”
江寻鹤缓缓合上了眼,眼角的湿润将长睫打湿,粘成一处。
他捏着信纸的手有些不自觉地发抖,这封信太过于沉重,是母亲将他从江骞那些打压的谎话之中拉扯出来,可却转头又将她自己沉入水底。
她与江寻鹤大约都没错,只是这世道利益交混、权势滔天,总是活了这个,另一个便浮不上来。
他今日就算是把两家的人都一并用作抵命,明日还是照旧会有无数个这样的女子、无数个这样的江寻鹤。
这世上需要的从不是多少个江家,而是数不清的楚家,而后才会有无数个管湘君和叶梅芸。
董嬷嬷叹了口气道:“夫人就睡在后面,公子要不要去看看?”
江骞何其吝啬,又何其恨这个没能被他榨干价值就草草离世的女子,还能修筑一处坟墓,他便已经觉着自己仁至义尽了。
江寻鹤将信纸收了:“你们守在这里吧。”
他独自一人去瞧了那冷情的坟墓,大约是因着董嬷嬷还时时看管着,所以还不曾生出什么破败景象,可对于一家主母来说仍旧是再寒碜不过——江骞就是故意用这种法子羞辱的。
可对于她来说,却未必不是一件幸事,就如同她给江寻鹤取的名字一般,她从未有一刻不在向往着自由。
——
楚家的商船已经离开了乌州,与此同时江寻鹤忽然回了江东的消息也传到了沈瑞耳中。
他瞧着那信上有些潦草的字迹便知晓江寻鹤定然是得了消息便匆匆赶过去的,他虽未仔细问过江家的情况,但手下却又耳聪目明的探子。
据说那江家老太太是那虎狼窝中难得嫩不过拎出一副好心肠的,虽然沈瑞瞧着实在是未必,但只要能装到死,给江寻鹤留下些念想却也不错。
“备车,去江东。”
他总不能守在中都,就这么冷眼瞧着那只漂亮鬼平白地被虎狼吞吃了。
他这人没什么太大的能耐,但一惯会用权势富贵压人,且对着江家那些个,只怕是更有效用。
*
马车总归是要比水路快些,可即便如此,沈瑞还是在半程的时候,便收到了江寻鹤时隔四日后的头一封信。
侍卫们收拾了吃食正在休息,猛一听见脚步声顿时便起身拔剑警戒,送信的人眨着眼瞧了好一会儿,才忽然惊喜道:“可是沈公子的车马?”
他原以为自己要一路到中都去,谁承想竟然这般好命,在中途便遇见了沈家的车马。
帘子被掀开一个边角,沈瑞只略打量了下便开口道:“江寻鹤派来送信的?”
“正是,东家命我给沈公子送信来。”
他一边说着,一边忙不迭地从怀中掏出那被包裹了好几层的信递到沈瑞面前去。
沈瑞接过信,看着那厚厚的一摞轻轻挑了挑眉,但还是耐着性子一层层剥开,最终落到他手中的也不过是层纸的厚度,同旁边拆解开的一大摞外壳形成了再鲜明不过的对比。
沈瑞轻“啧”了声,一边拆着上面的蜡印一边随口道:“江家而今可有什么变动吗?”
这才过去几日,料想也出不了什么大事,只是他心中到底担忧着江寻鹤,才这般问。
谁知那仆役却挠着头道:“老夫人病逝了,前家主伤心过度干脆剃度去山上做和尚,为老夫人祈福去了,而今江家已经是东家在做主了。”
沈瑞手上动作一顿,抬眼看过去:“剃度了?”
那仆役并未想太多,干脆地应了声。
沈瑞脸色却有些难看起来,他虽未亲自到过江东,但江骞为人如何,他确实再清楚不过,说他因着老太太去世而伤心欲绝剃度,简直是天方夜谭。
对外说是祈福,对内只怕是赎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