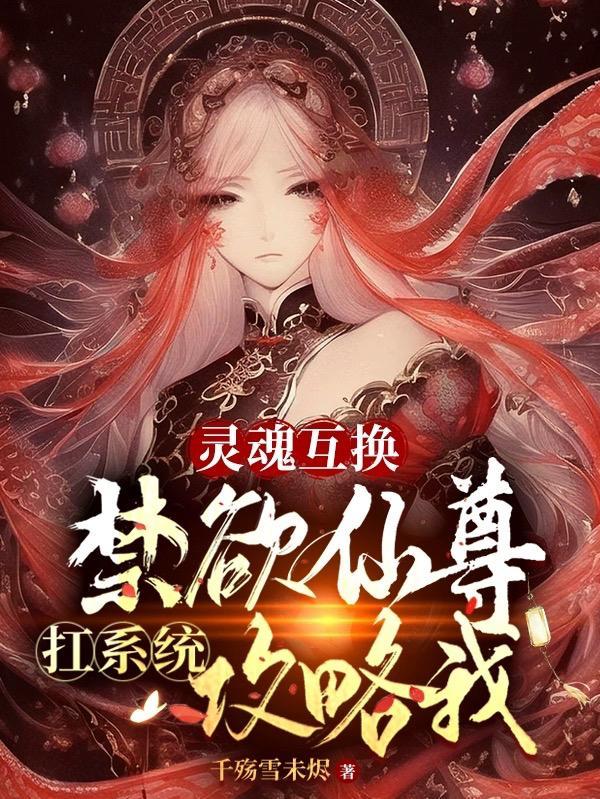大文学>御前皇后 > 第39章(第1页)
第39章(第1页)
戚永琛随着他的目光看去,自然也看到这一幕,他们看到了,想必满朝文武都将此情此景尽收眼底,只是个人都揣着明白装糊涂,依旧大口饮酒,豪言壮语,心中却都打起了小九九。戚永琛掰开一块点心,从中挖出一颗完整蛋黄笑道:“人如这饼,心是什么模样的,偏要掰开了,捏碎了才能看到。湮寂进宫也有些日子了,跟皇帝琴瑟和鸣,倒是令人羡慕。”
翟湮寂说:“名为夫妻,实为君臣,陛下厚待我,我忠诚于他,也就够了。”
戚永琛说:“这倒是真的,恭敬进退怎么也不会错,我知道湮寂最有分寸,不过姨母还是托付我嘱托你,对帝王万不可全心托付,帝心深如海,波浪无常,千万保护好自己。”
翟湮寂不知如何倒是想到了萧贺在皇帝面前的无所顾忌,还有皇帝对他自称我时候的随和自在,心中蓦然一紧,抿了抿嘴说:“我知道。”
戚永琛说:“立后已有快两月,皇帝那边有没有选妃的打算?”
翟湮寂说:“他未曾跟我提过。”
戚永琛用眼角别有所指地一点说:“我看他心中倒是早有看上的了。”
翟湮寂说:“纵使选妃,也要谨小慎微,李尚书的女儿未必合适。”
戚永琛嗤笑一声:“你当选妃是选后?皇后是站在皇帝后面的人,而妃拆开是女己,是自己喜欢的女人,只要皇帝喜欢管她什么出身。”
翟湮寂叹了一下:“他,他应当不会如此肤浅。”
戚永琛说:“他是帝王,天下都在他的掌控,伸手是云翻手是雾,什么都能轻易得到,怎么会压抑自己的喜好呢?”
翟湮寂心中不知为何,像是被一口气堵住,搅合的心中一股憋闷,他没有说话,反而端起酒杯一饮而尽。
夏涌铭和孟乔褚、李胜成三人坐在一处,他们当初是同窗,也还算有些情谊,但是自从各自为官后,渐渐生出几分间隙。但是面上仍然是一团和气,互相寒暄各自的生活,正说道热闹之处,一个声音打断道:“哎呀,今年的后选,各个出类拔萃,真是让本官大开眼界哇。”
正所谓哪壶不开提哪壶,三人不悦地朝着此人看去,萧侍郎笑眯眯地坐过来:“转眼间你们都长这么大了,真是岁月催人老啊。”
萧贺比他们最多也就大个三四岁,此时却充起大辈分,三人气得咬牙切齿,但是无奈官大一级压死人,也只好起身行礼:“下官见过萧大人。”
萧贺笑眯眯地说:“快请起请起,几位真是人中龙凤,哎,可惜可惜。”
虽然他们上殿后,从来没有看见过萧贺,但是这位声名狼藉的萧大人他们可算是有所耳闻,一张毒舌见人就损,完全不给同僚留一点面子,据说前年把户部的老尚书气的在朝堂上追着他打,皇帝罚他去老尚书家门口给人扫院子推车,结果他咋咋呼呼不光把老尚书家收受的贿赂全都翻腾出来,还顺手查出了老尚书儿子强娶民女的事情,最后老尚书只能告老还乡,放言说萧贺在一天,他便再也不上朝。几个老尚书的学生气不过,联名告萧贺,谁知道此人无家无业,无妻无子,连房子都是租的,每月供奉到手就花的精光,除了在朝中羞辱当朝大臣还真没有别的罪名,最后还是皇帝为了安抚人心把此人调去修大坝,才算安静了些。
宁得罪君子不得罪小人,在朝中最不能得罪的就是萧贺,不然谁知道他在皇帝面前会给你抖落出来什么。李胜成对孟乔褚使了个眼色,然后站起来说肚子不舒服,孟乔褚扶着他,俩人赶紧跟萧贺告退,萧大人笑眯眯的说:“皇宫内院的净桶干净如琉璃盏,两位贤弟可要小心,别滑下来,摔青了屁股。”
眼看俩人急忙遁了,夏涌铭也站起来想跑,被萧贺一把拉住:“小夏哪里去?”
夏涌铭没好气地说:“萧大人且放手,皇宫内院,萧大人如此拉拉扯扯的,实在失礼。”
萧贺笑道:“半年未见,小夏怎么脾气越发暴躁了?难不成因为没有当上皇后,迁怒于我么?”
夏涌铭剑眉道理,小声怒道:“萧贺!你再胡说八道,我把你舌头割下来。”
萧贺说:“冤枉啊夏大人,我哪里胡说八道了,当初你硬要去选后,我这心里刀砍斧劈一般痛,哎,这才去了江南自生自灭,好在皇帝他重情义,知道我倾心于小夏,特意没有选你当皇后,皇恩浩荡啊。”
夏涌铭被他调戏的怒从心头起,恨不得把他这张嘴撕烂:“翟湮寂做皇后本来就是计划之内,你、你再血口喷人,我就真的把你的舌头割下来。”
萧贺眯着眼笑道:“啊呀,我这舌头还是留着罢,以后你便知道它的好处了。什么计划,不要乱说,要是走漏了风声,该被割舌头的就是小夏了。”
夏涌铭气的脸白一阵红一阵:“你不好好在江南干你的事情,跑回来做什么?”
萧贺说:“养鱼虽然快活,也不能总养不捕,秋日到了,正是收网的好时节。”
夏涌铭见他难得正经的模样,坐下来拿起一串葡萄,有一个没一个的吃:“大坝建成了?可是要动手了?”
萧贺说:“太早,弄不好偷鸡不成蚀把米,皇帝满肚子心眼,才不会干没有把握的事情,还要再等等。”
夏涌铭别有所指的说:“可是我看有的人却按捺不住了,这脂粉美人计都用上了。”
萧贺说:“那是自然,帝后融洽,一旦丞相将兵权交给皇后,李孟就危险了,如今是牵一发动全身的时候,当然要想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