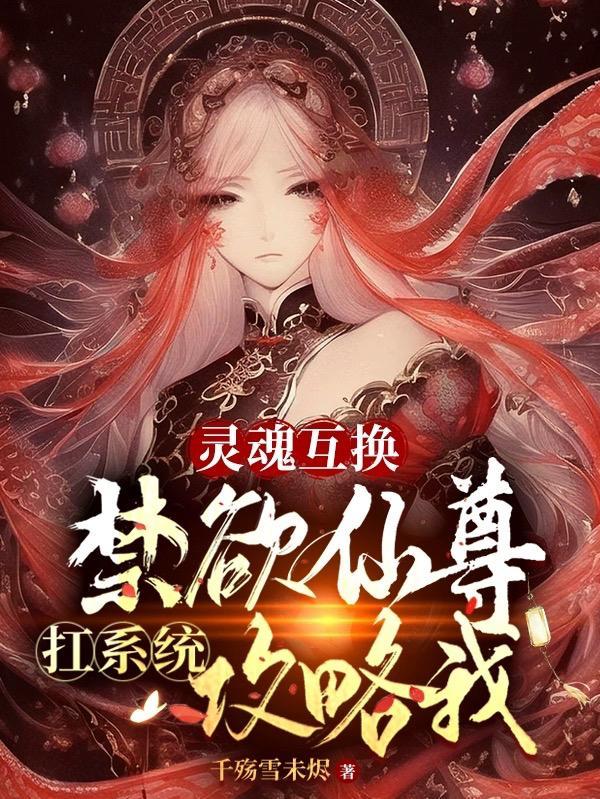大文学>谁没爱过傻逼 > 第50章(第1页)
第50章(第1页)
雪断断续续的落下来,先是细碎的小雪花,慢慢的变成了鹅毛似的雪片,扑天盖地的落下来。顾国泰掀开窗帘的一角往外看了几眼,顿时心头蹿上股说不出的感伤。他语文不好,翻来覆去也找不到华丽丽的形容词,就是觉得心里酸酸的。后来他倚在窗户那漫无目的地往外看,头一回觉得回忆是挺让人难过的东西。那不是暴几句粗口,喝几瓶酒就能解决的事,那是种明知道根在哪儿,却无从下手去除根的茫然感。
……
武文衔着根烟出现在林春身后:“想什么呢?不知道的还以为你玩雪人行为艺术呢。”
林春裹着件黑色的丝棉羽绒服,还是借大甲的钱买的,并且答应还钱时要请他吃顿饭。林春回头扫了武文一眼,突然问:“能给我根烟抽吗?”
武文丢了根烟给他,又帮他点上。林春吸了几口,说:“其实你人还行,你不挺烦我的吗?”
武文哭笑不得:“小王八羔子,你还记仇?”
“我啊,”林春顿了顿慢慢说道:“哪能跟小王八羔子记仇,那多没风度啊。”
武文抬脚就踹,林春习惯性的躲:“你这鞋不适合在雪地里跟人打,挺贵的吧,弄坏了我没钱赔你。”
武文将烟屁股弹到地上,又用脚踩了踩,说:“打得过我吗你?”
林春张嘴呼出口白气,那张棱角分明的脸躲在氤氲的白气后面,显得格外干净,有点像刚下完雪时四野寂静的样子。武文溜到嘴边的话生生咽回去,只留下个单音节回荡在空气里。
林春捡了根枯掉的树枝,蹲下来在雪地上乱划,不是画画,就是随手涂线条。没能回家过年,他心里多少有点失落。昨天晚上借二甲的手机往老家村里打了个电话,说工作忙,过了年再回去。他奶问他是不是没买上火车票,林春当时心里一阵泛酸,差点没哭出来。再想到许辉……他们是一伙的,为什么走的时候不带上他?不是说好一起回他老家过年的吗?
武文想调侃林春几句,谁想说出来却是:“我这两天回北京,你回吗?”
林春转头看他,脸上眼中满是怀疑:“你这么好心?”
武文挠挠头:“大爷可是讲理的,一码归一码,到底回不回啊?”
林春想了想,把手里的枯枝远远丢开说:“回呗,我没钱买火车票。”
“真穷。”武文笑了笑说:“你回去还去建筑工地?”
林春说:“对,被子衣服什么的还在那。”
“肯定土的要死。”
“洋气的我穿不出风格啊,天生不是那人。”林春脑海里突然浮现许辉的身影,辉子穿什么应该都挺好看的,这样想着他就傻乎乎的乐起来,看的武文一身鸡皮疙瘩。
林春傻的特真实,这让武文想起小时候听过的一个故事:某家大人让家里的小孩子出去买鸡蛋,小孩听话的买了一篮子。回去的路上有人跟他开玩笑:你篮子底漏了,小孩咦了声就翻过来看,结果鸡蛋掉到地上全碎了。武文觉得林春就像那个小孩,他接触的人都猴精猴精的,碰着个傻的,倒有点不适应。就像人习惯了转弯抹角的处理事情,慢慢的就会把所有事都想的复杂。
“喂,又琢磨什么坏事儿呢?”林春见武文那状态都快神游了,忍不住喊了声。
“管得着吗你,傻的啊,这么冷赶紧回去了,找大甲二甲打牌去。”
“我不太会打。”林春实话实说。
“说让你打了吗,你是那端茶倒水的。”武文边贫边扫了扫身上的雪花,弄的手上凉凉的。林春正跺着鞋上沾的雪,裤脚被雪水浸湿,弄的脚踝凉凉的。
……
许辉那天离开煤矿开采区后找了家小旅馆倒头就睡,直到第二天下午才睡醒。肚子饿的像唱空城计,他哼着不知名的唱曲出去饱吃了一顿。不是什么好饭,两碗刀削面,点了三个菜,可劲往肚子里倒。吃饱喝足后,顺便去附近的票点买火车票。售票员问他:“去哪啊?”
许辉说:“随机打,打哪是哪。”
那售票员用奇怪的眼神瞄他,许辉心想:嘿,准把我当神经病了。不过重获自由的感觉真好,整个人都轻飘飘的。心烦是必须的,但纠结心烦就不对了,起码乐完了再纠结。
售票员给他打出张去成都的,站票。许辉装起票,突然想到一件事,又折回去问售票员:“能换成西安到成都的吗?”
那售票员跟看怪物似的看他,换完票,许辉回旅馆退了房,直接去汽车站坐车去西安。到达西安的时候已经凌晨了,他在车站附近找了家旅馆凑和一夜,火车是第二天晚上的,他不着急。睡到自然醒,跑到zara买了身衣服换上,旧衣服揉巴揉巴丢到路边的垃圾箱里。许辉深吸口气,很好。
春运期间火车站人挤人,好不容易挤上车,里面更挤,连活动活动手脚都是奢侈。许辉望着满火车的人,他有点茫然,每张陌生的面孔后都有个故事,开心的失落的,个中滋味自己品尝。他不过是无数普通人里的一个,谁知道他爱男人?谁知道他的故事?就算天大的事,在不相关的人群里也变成了草芥。
许辉抄着口袋倚在两个车顶的连接处,有个抽烟的不小心把烟灰弹在了他衣服上,说了声对不起,许辉回了他句没关系。他不经意的抬头时,恰好看到那中年男人满面风霜的脸,那些粗糙的印记,比任何故事都来得有冲击力。许辉装作若无其事的低下头,后来请那男人吸了支烟。
没有惊天动地的爱情故事,那男的抽完烟,感慨了句:“现在日子不好混啊,干嘛都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