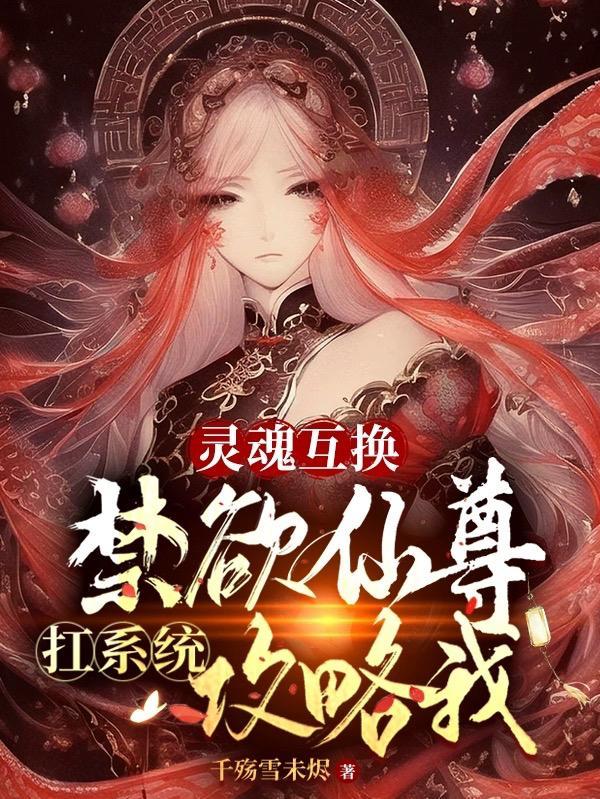大文学>貌美万人嫌总被窥伺(快穿) > 第97章(第1页)
第97章(第1页)
许迦叶担心弄脏了太后的衣服,松开手离了她的怀抱,用摸脸的动作隐晦地拭去脸颊上的泪水。
伴随着内侍的通报声,萧亦衍缓步入了侧殿,向太后行礼问安。
他的视线一直锁在许迦叶的身上,自然看见了她泛红的眼眶,沉声问道:“这是怎么了?”
许迦叶微不可查地蹙了蹙眉,从罗汉床上坐了起来,向萧亦衍行了个礼,看向太后道:“臣请告退。”
“予让他们送送你。”太后温声道,转头吩咐杨姑姑道,“你多带几个人帮迦叶拿着食盒。”
杨姑姑颔首领命。
“朕也送一送许卿吧。”萧亦衍说道。
太后瞥了萧亦衍一眼,淡声道:“皇帝还是留下吧,予有话同你说。”
在萧亦衍目不转睛的注视下,许迦叶渐行渐远,翻飞的衣角消失在了门边。
见许迦叶走远了,太后手指轻击了两下茶桌,沉声道:“皇帝,你消停了几年,予以为你已经断念,怎么如今愈发要去痴缠迦叶,是打量着予命不久矣,所以为所欲为了吗?”
萧亦衍往下首位置坐了,接过宫人奉上的茶,说道:“母后何出此诛心之言?儿臣日夜期盼您能福寿安康、万寿无疆。
“儿臣爱慕迦叶,情难自持,自然想日日夜夜同她待在一处,但儿臣发乎情,止乎礼,为所欲为却是没有的。”
这两年来他每每有了能与许迦叶单独相见的机会,都会在他身体里另一个灵魂以命相搏的干涉下功亏一篑。
那个人话说得冠冕堂皇,说什么绝不会让他伤害她,分明是他自己行将消散,便嫉妒他有机会与迦叶长相厮守,宁可保下裴玄澈,也要给他添堵。
幸而那缕残魂已销声匿迹,许是魂飞魄散了也说不定,他终于可以见她,简直恨不得像猫儿狗儿一样跟着她。
太后眉头紧蹙:“你说的爱慕,便是两年前趁她兵败,欲借机夺她兵权?若不是你生此念头,当年迦叶岂会支撑得那般幸苦?”
萧亦衍用杯盖拨了拨茶水,抬眸道:“朕绝无此意,只是想让她留在京中好生休养罢了。迦叶伤病缠身,儿臣怎能坐视她拖垮了身子。等她的身体养好了,她想去哪里、想做什么,自然都由得她。”
让她在他眼皮子底下横遭此劫,落得一身伤痛,已是他无能,若他连她的身体都顾及不好,那他还活着做什么?不如死了算了。
太后长叹了一声:“你可知人的心气便如蜡烛的烛芯,心气一旦没了,烛火便长久不了。你没有资格替她做选择。”
萧亦衍沉声道:“朕是皇帝!”
太后冷笑道:“你是想同她结为连理,还是想与她永为君臣?出发点错了,步步都是错。”
萧亦衍一时无言。
灯影摇晃,天地静默无声。
*
出了宫门,没了高大巍峨、层层迭迭的宫殿的阻挡,寒风呼啸之声渐起。
许迦叶抬眼望去,裴玄澈正静立于马车旁等待她,身穿一袭宝蓝色云锦银丝暗纹团花长袍,戴了一条饰以珠玉的抹额,潇洒俊逸如风拂玉树。
裴玄澈望见许迦叶的身影后两眼一亮,三步并作两步走到她身边。
他把她从头到脚打量了一遍,见她眉眼间有些许疲惫之色,心疼道:“怎么这么晚才出来,一定累坏了吧。”
许迦叶轻声道:“太后召见了我,与殿下待在一处,时间不知不觉便过去了。”
裴玄澈这才发觉许迦叶身边站着杨姑姑,他颔首致意,温声道:“殿下对侯爷的照拂之情深如渊海,令人感佩。”
“殿下曾言,侯爷出类拔萃,担得起万千荣宠,她不过护佑一二,不足为道。”杨姑姑笑道。
她指挥着宫人们将食盒放进了马车,与许迦叶作别,临别前深深看了裴玄澈一眼。
殿下担心裴玄澈性情桀骜,伺候不好人,她瞧着却不尽然,回去后她要说与殿下知晓,也好让她放心。
许迦叶见杨姑姑望向裴玄澈的眼神意味深长,也认真地瞧了他几眼:“怎么这么一会子功夫,你就换了一身衣裳。”
天都黑了,还穿得像是要去赴宴一样,无怪乎让人觉得奇怪。
裴玄澈压了压上扬的嘴角,他每日都精心打扮,终于被许迦叶注意到了。
“舟车劳顿,上一件衣裳沾了灰尘,我便随意找了一身新的换上了。”
他说得轻描淡写,其实这袍子他挑选了许久,抹额也是好不容易才搭配好的。
许迦叶微一点头,裴玄澈想怎么穿是他的自由。
她绕过裴玄澈走到马车前,对向她行礼的车夫微一颔首,一甩衣摆上了马车。
裴玄澈快步跟上,一同进了马车,坐到了许迦叶身边,他本想同她说说话,但见她疲倦地阖上了眼,便噤了声。
车轮滚动声打破寂静,马车向前驶去。
车帘随风飘动,月光洒下清辉,许迦叶的睡意被风吹散,她半睁开眼,低眸凝望着透过车帘缝隙漂浮游动在她手背上的如练月华。
“我初从军,入定远军丙字营,定远军是当时唯一一个有女营的军队,世人皆叹其标型立异,少有人记得,二十几年前,这一支军队完全由女子构成,当今太后便是其主帅。
“倘无殿下开此先河,彼时我势单力薄,大抵只能女扮男装入军营了,不知又会有多少险阻。”
裴玄澈注视着许迦叶月光下光洁如玉的侧脸,声音温润如和风细雨。
“军营就在那里,可铁了心从军的人寥寥无几,你能承蒙太后恩泽,说明天助自助者。你是我见过最一往无前的人,与其他所有人都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