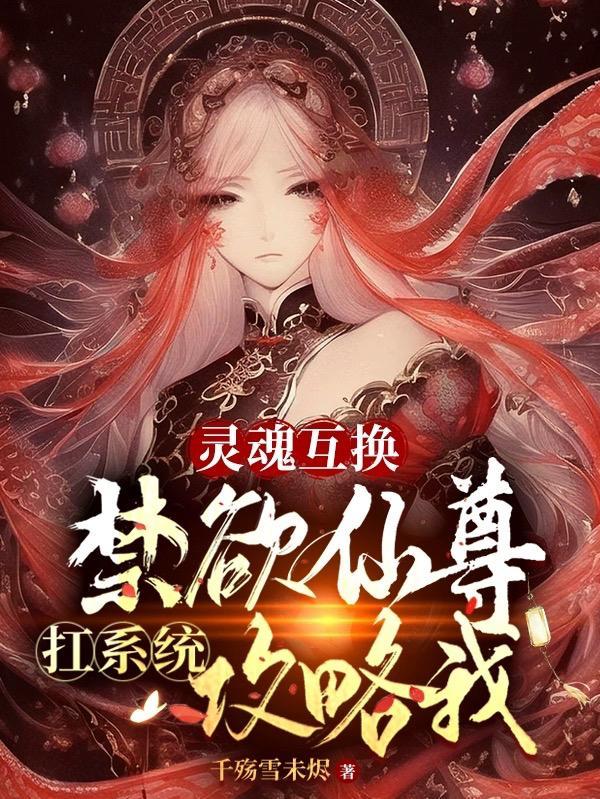大文学>精灵大学 > 第9章(第1页)
第9章(第1页)
白霄心虚地点了点头,其实她家就住在青丘里,还有她真的需要嘱咐。
凌晨出发,一路睡过去,清早下飞机。
候机大厅循环播放着:“旅客朋友们,欢迎来到西岐航空,祝您旅途愉快……”
西岐机场。
白霄回头看了眼四个字,淡定地打了辆出租车。
“师傅,白家涧。”
老家还是她熟悉的样子,门口的梧桐树枝繁叶茂,大黄狗老远就闻到她的气味,狂摇尾巴冲了过来,狗子伸长一米二,高过小腿,肌肉粗壮,毛重六七十斤,差点把她撞倒!
梧桐树上拴着的老黄牛看到她也“哞”地甩了下尾巴,白霄本以为老黄是因为见到她开心,再看才发现老黄是想赶走屁股上硕大的牛虻。
她走过去帮忙拍掉牛虻,老黄又湿漉漉的鼻子顶了她一下,这下倒好,狗子没扑倒她反而被老黄撞倒了。
白霄龇牙咧嘴地爬起来,撸了一把牛头。
她家住在白家涧唯一一个瀑布边上,枯水期经常断流,景色也说不上好看——原本是这样的。
但世界变了,人与妖共生的世界自然资源没有遭到过度破坏。树更茁壮,草更翠绿,花更鲜艳,乘坐短途汽车回家的路上,甚至看到二十多只梅花鹿旁若无人地穿过水泥路,停下来等鹿群通过,许多乘客都拿出手机拍照,她也不例外。
像误入森林公园。
她家还是个大家族,靠山吃山,舅舅家开了家‘白家涧民宿’,旅游旺季才能勉强糊口,最大的依仗“飞瀑连珠”小筑,建在瀑布边上的猎人小屋很像,配有壁炉和吊床,还有十几亩茂盛的向日葵田,每到旅游旺季,这里的确是水声潺潺、繁花似锦,蚊子和牛虻一样大,即使撒上药粉也有各种虫子光顾,她怀疑山里的虫子十几年下来进化出了抗药性。
白天还好,到了晚上没有适应瀑布溅落声的游客八成是睡不着的。白霄还好,她在这里长大,多少习惯了激流飞石。
回头客几乎为零,少有那个几个来的,都是本地的年轻人,或者省内的穷学生。
这个点家里肯定没人,亲戚们都上山摆弄茶树去了,白家涧自然不能光指着旅游业为生,全村几百口人还不得讨饭去。
白家涧以茶树为主要经济作物,特产是秦巴雾毫,传说是用少女亲口菜的嫩芽炒至而成,白家涧的游客也是这么听说的,然而据白霄所知,白家涧因为人口老化和外流已经十年没有少女了,留守的都是至少四十近五十的中青年,茶叶盒子上印的美貌姑娘是白素胭女士二十几年前的旧照……当然她现在还长这样。
然而,白女士,表示自己从来没干过用嘴巴摘茶叶这种事,效率太低了。
说起采茶,她小时候还在茶园里遇到了狐貍,不过是只黄白色杂毛野狐貍,那狐貍戴着一顶济公同款的靛青色帽子,脖子上挂着一串珠子,蹲在一株最老的古茶树下,问白霄它长得像人吗?
白霄哪敢说不像,说完忙不迭地跑了。
这事过去近二十年,她反复提起父母都只当她做了个梦。将梦境和现实混淆了,可自打身份证上的籍贯变成了西岐市青丘镇白家涧,白霄越发不敢当那是个梦了。
哪个时空她都有十几年没回来了。
老房子落了一层灰,邻居把钥匙交给她后,白霄像打开尘封的记忆似的推开了榆树木门。古铜色的风铃依然清脆。茶瓯香篆小帘栊还维持着主人曾经使用过的模样,未动分毫,墨迹早已结痂,白霄取了点水倒进砚台中重新研磨起来。
砚台内部有几条裂纹,白霄眯着眼儿,想起小时候往里放过鞭炮。她还炸过狗盆,她绕到屋后柳树下,从倒塌的红砖狗窝里翻出被黄土掩埋的狗盆,狗盆还在,狗却早已不见了。
咳咳……
依次打开所有窗户,层层迭迭的黛色青山宛如最美好的风景画。
“真好看。”
但很快,沉迷打扫的她就笑不出来了。
到处是灰尘,看来邻居只有定期通风,而已。
她拿着竹竿戳了戳房顶,哗啦啦掉下来几片松动的瓦片,还有一堆弯弯曲曲的蛇蜕。
不要怕,这是保家仙、看家蛇,无害的,白霄心头狂跳,闭着眼睛把大自然的馈赠收拾了起来,蛇蜕可以卖钱!
但是屋顶的破洞——
她开启大召唤术:
“哥啊!下雨了修房顶了。”
被巨兽一脚踩坑里里,只是那巨兽足弓高,没踩结实,唐青侥幸活了下来,正在家里养伤。
她这个表哥身世复杂,姑姑没有孩子,跑遍了各大孤儿院才领养到了唐青,唐青十岁时姑姑姑父车祸去世,唐青就在白家涧吃百家饭长大,他运气也很糟糕,总是倒霉,山坡滑下的石头总是会砸到她,撞上蛇的总是她,起码白霄长这么大一条野生的蛇都没见过,而唐青一个月能看到七八回。即使如此,唐青也没颓废,每天都努力生活,感动中国暂时不能,感动白家涧是没问题。
唐青住在镇子上,离白家涧只有十几分钟的公交车,白霄炒了两个菜装进饭盒,去镇上送温暖。
青丘镇,原本自然是别的名字,镇子还算繁华,刚下车,车站附近各种早市摊早点的香味争先恐后的钻进鼻子,白霄走不动了。
她随意挑了个饭馆,叫了碗扯面,吃完了又跑到隔壁喝了碗驴肉汤。
“老板,加个馍!”
一路上吃的肚皮溜圆,老家的物价可比凤凰城便宜多了,七拐八拐地才到唐青的小院,唐青这个人很有把平凡的生活过得浪漫的诗意,穿着白麻布做的茶服躺在摇椅上,提前五十年享受起晚年生活,地上还扔着几个外卖盒,比狗舔的还干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