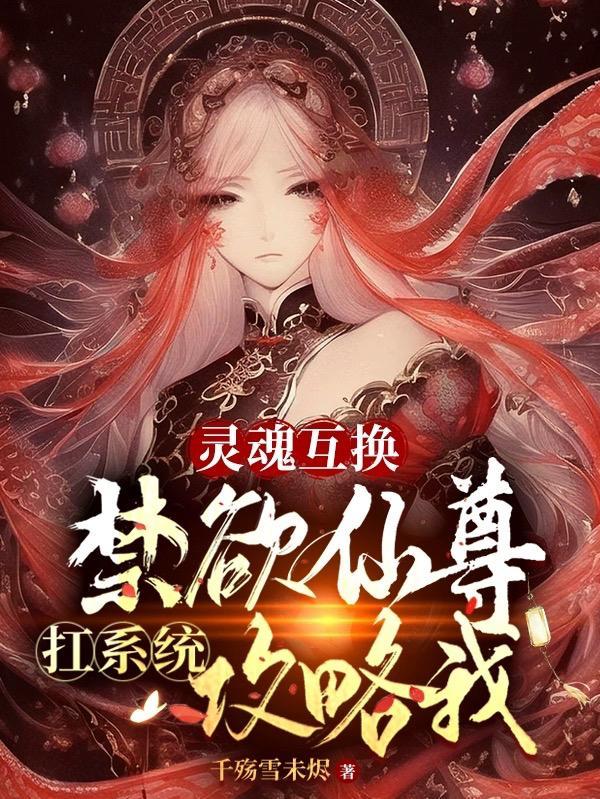大文学>追到太孙殿下我失忆了 > 第95章(第1页)
第95章(第1页)
“老王八迟早死在臭丫头手里。”最后这一声仿佛是从嗓子眼里说出来的,暗哑艰涩。
梁飞若转过脸,抬手抱了抱她的头送到自己的肩窝,轻拍。
屋外寂静无声,一道黑影闪过,仿佛是错觉,不留痕迹。
古大师
寒风呼啸,夜里开始降温。
隆冬已至,白日里路上已少见行人赶路,该回家过年的早就到家了。
村镇里反而热闹起来,杀鸡宰羊,热热闹闹,准备迎接新年。
入了夜,一切归于寂静,寂寥空旷,人心都跟着无处安放了。
巷口的一家酒馆,黄色陈旧的酒旗结了冰冻成褶皱的硬布块。本该早就歇业。奈何客人给的银两实在多,照旧点了灯。十几坛的烧刀子酒,摆成一圈。
客人也不为难他,让他自去歇息了。
店家起先还撑着,后来实在受不住困和冷,打了声招呼自去后堂眯一会。
男人眯着眼,本是一副酒醉不醒的模样,某个瞬间,手背青筋紧绷,握住桌上的刀柄,猛兽般的眸子犀利如刀。
“原来蒯指挥使在这喝闷酒呢。”来人轻声一笑,清丽的面庞唇色红艳。
蒯宗平一惊,收回视线,起身行礼。
梁飞若一只手撑着窗口,一跃进了屋内,端坐在对面,自行斟了一碗酒给自己。
“寒冬腊梅,指挥使好雅兴呀。”
屋外一株歪脖子红梅,花骨朵都被调皮的孩子打落了,零星的几个开在枝头,孤孤单单,实在称不上美景雅兴。
梁飞若仰脖喝了一碗,一只手朝蒯宗平挥了挥,“快坐下,指挥使不必如此拘谨。啧,好辣。”又望向空荡荡的桌面,“有酒无菜,伤身呐。”
蒯宗平一直绷的笔直,“属下这就喊店家起来做菜。”
梁飞若轻声叫住他:“人都已经睡下了,又何必再扰人清梦。我去厨房看看还有些什么。”边走边说:“指挥使可有什么想吃的?”
她走的很快。
蒯宗平拿起油灯,紧随其后,追上她,心中复杂难安。
刚到厨房站定,梁飞若手里抱着一盆饼,笑眯眯道:“指挥使好口福,一大盆羊肉饼呢,不过都凉了,冻硬了。无妨,加热一下就能吃了。”
蒯宗平想说自己不饿,又怀疑是梁飞若自己想吃,迟疑着该开口阻拦还是伸手帮忙,又不知该如何下手,梁飞若已解了披风摞他手上,“等我一下,很快。”
梁飞若熟练的生火,锅里淋油,加热。一个人锅前灶后,竟也游刃有余,丝毫不显慌乱。
这让他想起了一个人,那段日子二人同行,虽一路争吵互相看不顺眼,但每到饭点,那人都能化腐朽为神奇。相比较之下,蒯宗平就是猪狗刨食,管饱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