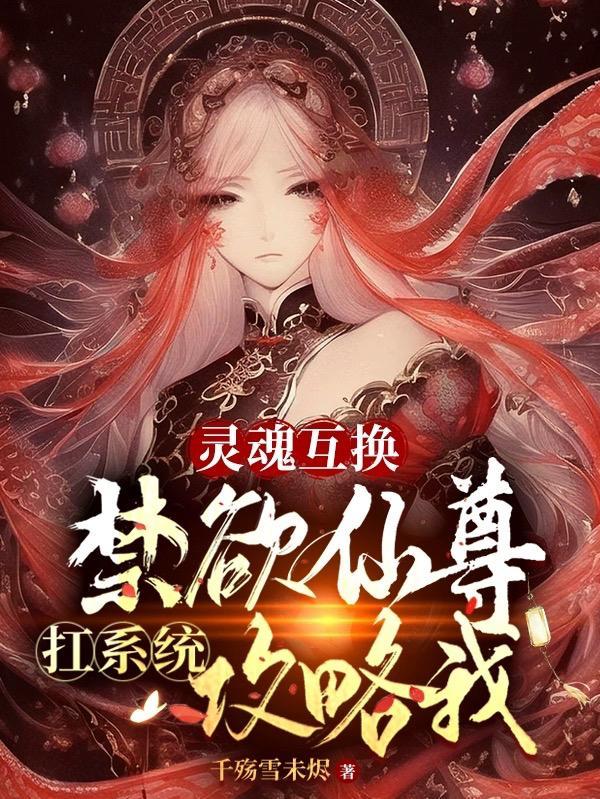大文学>人生苦短,必须性感 > 第93章(第1页)
第93章(第1页)
天不遂人愿,连恺丝毫没有犹豫,顺着滕刚的话道:“好,你回去就把今天看到的告诉我妈吧,连家我爸不做主,那就看我妈怎么处理吧。”
滕刚哑口无言,最后唯有摆摆手,转身退出了病房。
连恺面色凝重地看着门口,实际上内心却波澜不惊,他回身躺下,掀开被子把艾飞拽进了怀里,笑着说:“醒了就醒了,还装啥啊。”
艾飞艰难的睁开眼睛,担忧道:“你怎么跟你舅这么说话啊。”
连恺看着天花板,浅笑道:“他活了快半辈子了,啥事儿没见过,心里承受能力好着呢,不用担心他。”
“那你妈呢,你真打算让你舅告诉她?”
连恺撅了撅嘴,“我舅这个人脾气直,回去一准得告诉我妈,结果我已经想好了,挨骂或者挨揍是必须的,最多生我几天的气,也就过去了。”
艾飞有些话实在不好开口,连恺似乎洞穿了这一点,揉着他的脑袋说:“想说我残忍?”
艾飞看着他没说话。
连恺叹息道:“是挺残忍的,不过事情已经发生了,总得面对是吧,如果我听了我妈的话,以后结婚生子了,而我心里还想着呢,那我还是个人吗,害一姑娘这种缺德事儿哥干不出来。”
连恺见艾飞没说话,又说:“不结婚是不行了,我这个人注定不能单身一辈子,得找个伴,既然我喜欢男的,正好你也愿意,那就跟了我吧,哥不亏待你。”
艾飞一咧嘴,“你在梦里结婚吗?”
“操,干嘛在梦里啊,我妈要不同意,那咱就先这样,等她同意了,咱就办个婚礼,亲朋好友都请着,老子要怕他们一个眼神一句讲究,那我连恺的名字就倒过来写。”
艾飞有些哭笑不得,“越说越起劲儿。”
“哎,哥就是这么硬挺。”连恺大笑,“行了啊,家里的事儿我摆平,你呢眼前还有个重要任务。”
“啥任务?”
“搞定艾叶啊。”连恺故作担忧道:“叶子可是个狠角色,你得负责帮我搞定小姨子,不然我咋进门啊。”
“滚。”
连恺笑了笑,又说:“一提起叶子我倒想起个事儿,我昨天晚上出事以前,还看到过叶子呢。”
“在哪啊?”
“就在电影院那边的路口,我看她跟一个男的,而且还挺眼熟的。”
艾飞想起昨晚找连恺的目的,忙说:“我昨晚也发现了,一时间没了主意想跟你说来着,结果就……”艾飞顿了顿,继续说:“你说你看那人面熟,知道是谁吗?”
“记不起来了,不过我总觉着在黄朝那边见过。”
“你说什么?”艾飞猛的坐了起来。
就在艾飞和连恺担心艾叶的时候,一件大事发生了。连恺身上的伤虽然多,但都不算很严重,第三天他办理了出院手续回家了。医院大门口,连恺和艾飞短暂的分别颇有点难舍难分的意思,两个人一左一右的看了好半天,最终还是艾飞的狠了心一扭头走了。
连恺心想,如果艾飞这小子不走,他们是不是会在这里看上一天。事实证明,还真有这个可能性,以连恺对自我的评价,这种肉麻且滚刀肉的方式,他绝对是做的出来的。连恺住院这几天里,除了滕刚以外也就石头和王闯经常过来看他,不过来的时候大多数都是两手空空,连一件厚点的衣服都没带过来。连恺坐在车里,穿了件灰色的短袖,一边开车一边摇下了车窗,秋季冷风萧瑟,不仅吹走了夏季的炎热,更吹落了树上原本生机勃勃的叶子。
一片杨树叶被吹进了车内,连恺瞥了一眼,腾出一只手将那片叶子拿了起来,掐断了叶子的根。记得小时候,连恺经常会收集杨树上掉落的大片叶子,因为只有这样的叶子根部才是最粗大的。那时属于小孩的娱乐项目有很多,不过大多数都是不用花钱的,连恺就与石头和王闯他们经常用杨树叶的根来切磋,两根交叉,用力拽着两头,谁的从中断开谁就输了。遵照以往惯例,输的人是要请吃冰棒的,那时候便宜,五分钱一根,足够让几个人乐呵半天的了。
连恺追忆年少,不禁感叹时间匆匆,他从一个只知道吃喝玩乐的少年渣滓变成了愿意为感情赴汤蹈火的男人,这一变化是他自身值得骄傲的地方,可是……愧疚也时刻伴随着连恺,对于家里,他该如何交代,他该如何面对自己的妈,纵然他和滕刚说了一番狠话,实际上,他真的很难下的了狠心去办。
连恺幻想了一下老娘知道了这件事后的样子,凶神恶煞实不为过。
正如连恺猜测的这样,滕刚当天晚上回去就把连恺和艾飞的事情一五一十的告诉了连恺的妈。连恺妈叫曹玉兰,没嫁给连恺爸的时候还是个淑女,不知怎么地嫁了人以后,彻彻底底变成了河东狮吼。
曹玉兰脾气火爆,连恺小的时候挨打挨骂如同家常便饭,不过连恺心里深知,他这个妈是爱着他疼着他的。另外,曹玉兰还是一个洁癖非常严重的人,几乎到了走火入魔的地步。让连恺记忆深刻的是,有一次连恺回家坐在了曹玉兰刚刚铺好床单的床上,并且只做了一个角而已,再等连恺起来准备去喝水的时候,床角的床单被坐出了褶皱,然而就是因为这样,连恺被曹玉兰拿着鸡毛掸子一顿胖揍。
连恺抱头鼠窜,一个劲儿的吆喝道:“妈妈妈妈哎,我又没弄脏你打我干嘛呢。”
曹玉兰给出的答案更直接,“你屁股长钉子了,以后给我坐地板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