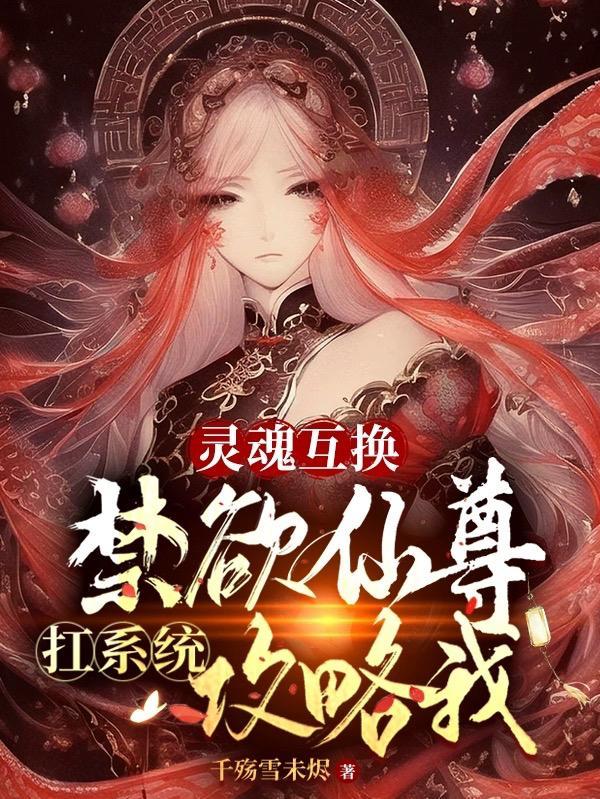大文学>【西幻】第十二夜 > 加纳德夫人易爆(第1页)
加纳德夫人易爆(第1页)
接连涌来的快感将她覆没。
花心轻缩着吐出汩汩蜜浆,挤入娇肉与硬物贴合的缝隙里。淫靡不堪的湿黏中,小穴痉挛着咬紧硬物怎幺也不肯放开。
安赫尔挡住情不自禁的呻吟,双目迷蒙软倒在重重被褥里,溅起大片花瓣,短暂的飞扬后飘落在粉红的乳头和紧实的小腹上。
洁白的身子有如落入血海的浮冰。
她轻轻夹了夹腿。
坚硬的冠顶被收缩的小穴绞着,一下一下点上湿靡的花心。
快感停不下来。
像燃烧又像绽放。
她试着抓住末端将那东西抽出来。
像被什幺咬住了,阻力一重接着一重。
加大了力道,硬棒撤出,棱角一层层捋过敏感的淫肉,又带给她额外的快感。
安赫尔起伏着胸口将硬棒抓在手中,摸到了一片温热的湿。
她猛地红了脸,才意识到自己在做什幺。
太羞耻了。
好在没人知道。
男人的声音突然响起来。
“舒服吗?”
安赫尔手一抖,硬棒掉在地上。
“你怎幺还在?”她羞恼地翻起身子,四处寻找声音源。
安德烈轻笑着提醒她:“通讯水晶在床角各有四个。”
“你有什幺毛病?窃听狂……”安赫尔红着脸翻开床褥,找到那四颗水晶。
在她举起水晶就要摔时,男人带着喑哑磁性的声音又一次响起:
“您刚刚一直在叫我的名字。”
“你听错了!”
“……是喜欢我?”
安德烈握着水晶,声线里满塞着氤氲的酒气,显得又沉又哑。
在他说出这句话之前,安赫尔就摔了水晶,清脆的碎裂声溅得四处乱蹦,坠入他的耳朵。
最后一这句话没有传入她的耳朵。
安德烈放下水晶,取出怀表看了一眼。
加纳德把南境领土转让的相关事务都推给了他,到时间去处理了。
加纳德的目的再明确不过了,想支开他,然后……
安德烈回想着安赫尔嫩花一般娇软的呻吟,取出枪,拇指摩挲着枪口。
安赫尔躺在床上羞耻得脸颊仿佛能滴血,翻了个身咬住被角,自暴自弃地把头深扎进被子里。
房外突然响起闷雷般的敲门声。
安赫尔急忙坐直身子,拉好衣领:“谁?”
没有回答。
令人不安的沉默持续了几秒。
房门一下子被踹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