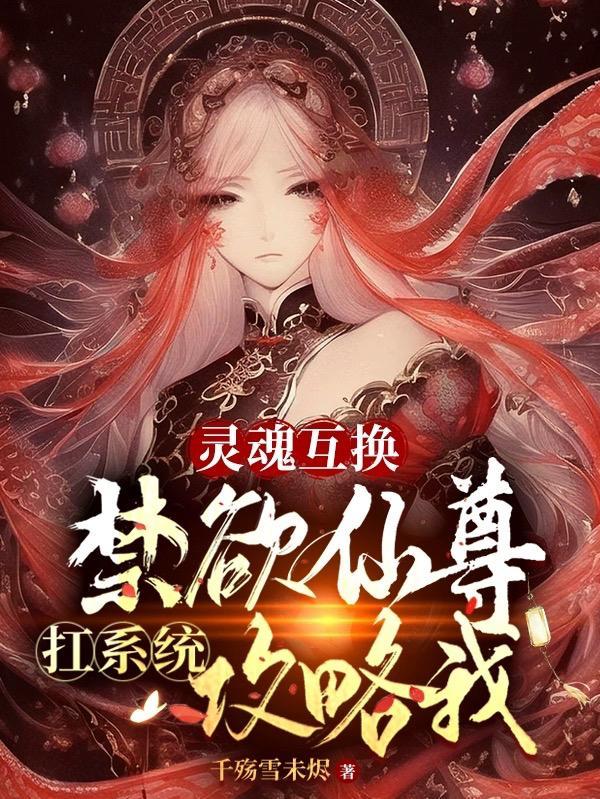大文学>死遁后我靠无情道飞升了 > 第90章(第1页)
第90章(第1页)
“好,今日去看。”
“爹爹最好了!”
朝思暮想的人就在上面,可池应淮却生不出胆量去看,在听到声音时甚至想要立刻逃走。
但脚下仿若生了根一般,让他挪动不了半步,直到两人缓缓走下来。
池应淮觉得自己的脸色一定很难看,以至于走下来的幼童面色警惕地看着他,然后站在了温清川前面。
“岁桉,不可这样。”
池应淮看着一身青衣的温清川,将孩童往身后一带,而后温和又疏离地看向自己。
“这位仁兄可是在山中迷了路?若是不嫌弃的话,可向在下陋舍内饮一杯茶歇歇脚。”
池应淮只觉喉间酸涩,直直地看向温清川,过了许久才干涩地应道,“多谢了。”
百年后
“且说百年前,人魔大战,那可是闹得人心惶惶,竟是连避世的镜花水月都惊动了起来,三界大战一触即发,却被一人给抬手制止,就此成就天下祥和的景象。此人便是神域身负天眼的神子——上清仙尊,只可惜英雄气短,以身饲魔封印十三魔族于鸠千夜后,便化作烈火燃尽天下邪祟羽化而去。”说书人叹息一声,捋了捋长胡子。
“我可听说那魔君与上清仙尊有一段情缘,连这大战都是因为上清仙尊逃婚而去才下的,可谓一怒冲冠为红颜啊。”堂中传来一声略带不明意味的笑声。
“可那上清仙尊怎会和魔君窝在一起?”有人不解地问。
原先发问的人站起来嘿嘿一笑,眼珠转了一圈,眯着眼说道,“听说那魔君在神域蛰伏时便将上清仙尊一颗心都勾了去,不然堂堂神子怎么会留神域叛徒在外逍遥十年任由其发展成魔君?况且我看那上清仙尊也没有你们说的那般好,不然他怎么会跟魔君勾搭在一起,我听闻那魔君如今已经被天惩堂释放了出来,指不定是两人做了一场戏来为魔君洗清罪责。”
“只可惜,还是上清仙尊被情爱蒙蔽了双眼,没能看清魔君的真实意味,而被抛了出去,成为了人洗白路上的垫脚石啊。”此人咂摸了一下嘴,唏嘘地说道。
众人听他言论,虽不知真假,但对上清仙尊也不再似方才那般认为其高洁不可攀。一些念头被散播出来时,无论真假,都如在人心中种下一颗会随时发芽的种子。
“我还听说……”那人像是又想起来了些什么,神神秘秘地说了起来,一时间竟是把茶楼内几乎半数人的心思都从说书人上转了过来,想听他再说出些那谪仙般人物的辛密事来。
茶楼角落里,一个穿着黑袍的人,手指把玩着一枚玉扳指,左手在茶杯上一点,竟是凝气出了一滴水珠来,悬在空中,从他的方向看去正对着还在肆意说话的男人。
“嘭——”
一个瓷茶杯从一旁飞出来,不偏不倚地砸在说话男子的头上,那男子原先身体前倾着和人说话,被这措不及防砸了中,身体踉跄往后退了一步,被身后的长凳子绊倒在地,直接摔了个四仰八叉,好生狼狈的模样。
刹那间,茶楼里发出一阵响亮的哄笑声。
“哎呦!是那个小王八羔子敢砸老子!”男人面子上挂不住,被人哄笑得涨红了脸,捂着额角慌忙起身,环顾四周寻找着动手之人。
“是我砸的。”清澈的少年声吸引了茶楼内人的目光,连说书人都停了下来,像是等着看两人之间摩擦。
悬在空中的水珠也落了下来,在木桌上砸出了个阴湿圆面,黑袍人微微抬眸,看向不远处站起身子来的少年。
少年穿着一身靛蓝色长袍,玉冠高束,长长的马尾落在□□的后辈上,衬得他长身玉立,腰间陪着一把长剑,指腹处能看出薄茧,是个习武之人。
身上的衣着虽不是什么华贵的衣服,但也能看出来是家里宠着的,整个人都透出矜贵张扬的气质来。
他褐色的眸子闪着亮光,此刻却带了些少年压抑不住的怒气,面容严肃地看着那捂着头的男人。
“上清仙尊以身饲魔,为天下百姓谋取福祉,纵使是那没什么底线的魔族来也是要敬畏一番的,你是什么东西在这里散播这等谣言来肆意抹黑前人?”
少年声音透亮,瞬间响彻了整个茶楼,连那男子被他说的都有些呆愣住。
“你又在这里出什么风头!不过是一个连毛都没长齐的臭小子,也能教训到我头上来?你怎么知道我说的不是真的?”男子脸上挂不住面,梗着脖子问道,“你们谁在百年前见过那场景?你们又真的了解事情真相?那凭什么说我所言为假?!”
周遭人被男子问了一圈,都没人回应,但也没人反驳,男子眼中闪过一抹精光,抬起下巴看向少年,“你若是今日给我道歉,我便不跟你这娃娃计较,否则我们就衙门见!”
少年闻言倒没有一丝慌张,而是从行囊中掏出一本被翻过无数遍的书籍,拍在桌子上。此时茶楼的人都在等少年的回应,见人有所动静后纷纷探出头去看那桌子上的书籍。
之间那书籍上大写的两个字——仙史。
顿时间将周围的人都惊了一下,互相看了一眼,不敢说话纷纷离那男子远了一点。
仙史为神域之人所做,记载的都是三界要事,神域之人几乎人手一本此书,但乐人间并没有,因为乐人间都是普通人,了解太多仙史恐引来无故之祸端。
既然面前的少年拿出了这本仙史,那便证明此人为神域之人,一时间谁都没有看戏的心思。
因为百年前人魔大战闹得太大,三界之内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不少乐人间的百姓都以泪洗面惶恐地呆在家里不敢出门,但最后什么也没发生,仍是一派祥和,再然后三界签订和平条例,彻底安宁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