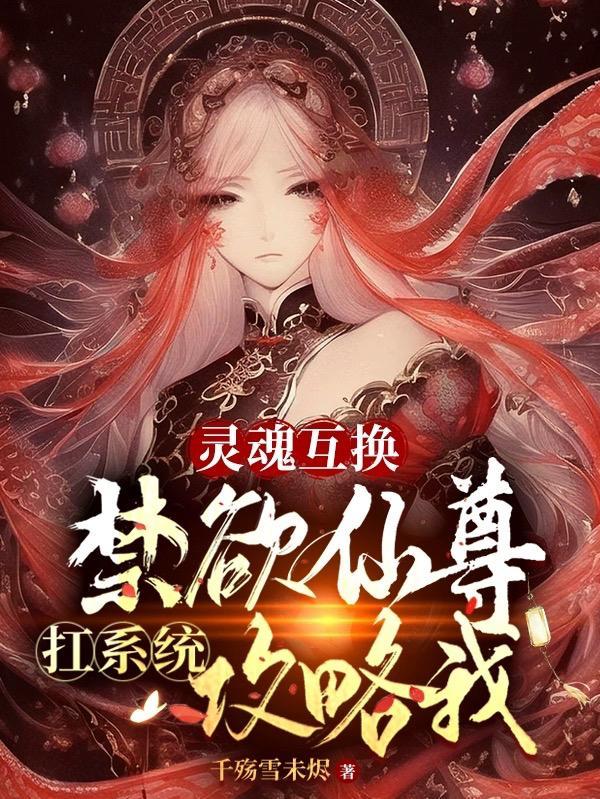大文学>东极西鄙 > 第296章(第1页)
第296章(第1页)
为什么身后的脚步声没有了?江匪浅转过身,林砧停在几步之外,站定,看着他。
“怎么了?”江匪浅问。
“你曾经是这么想的?”林砧直接问。
“是,但那是很久之前的事情了。”江匪浅的笑容堪称和煦,这让林砧有片刻的恍惚,脑海中闪过十方街初相见时候江匪浅的谨慎和含蓄,出使左土之后的冷厉和决绝。
“那不是很久之前的事情,直到现在,你还在困惑着。”林砧刻意和江匪浅保持着距离,似乎这样就能让他明明白白地看清自己和对方。
“有些事情,我从未和你说过,现在不妨说一说。”林砧忽然道。江匪浅睁大了眼睛,呼吸有瞬间的错乱,像是公堂上的人即将接受审判。
“什么?”江匪浅问,声音中有点颤抖。
“我们认识不久,我从神道中将你救下来,那时候我觉得,我和你很像,你就像是世界上的另一个我,我心里的执着、偏执和委屈,都被你用你的执着和偏执给说出来了。我曾经把你当一个小孩子,照顾你,因为我责任在肩,我以为后土的千钧命运系于我一个人的肩膀。我紧张,不敢松懈,将任何人的好歹都和自己的责任相勾连。”
“后来知道了你的身份,看着你和左土之间的联系越来越深,后土的命运从我肩膀上移开了,我有点小失落,觉得自己没什么用处了,但是后来我想通了,我总是要为后土身死的,派上什么用处都算数。但这时候,我反倒没法把你当作孩子了,因为你有了我没有的手段,还有一个冷静的头脑。”
“我一直以为为后土身死是我很容易做出来的决定,没什么后悔的。真的,直到我变成神树,我还是这么想的;直到我重新活过来,我还是这么想的。但是这些年中,我却常常梦魇”
林砧伶俐的口舌难得停顿了,江匪浅轻轻地说:“我知道。”但他从没问过。
林砧深吸一口气:“似乎直到这时候,后怕这种东西才找上了我。我梦到过你等我,梦到我我在长长的睡梦中见到的和你的诀别,梦到过我真的不在了之后两块土地还有你。第一次梦魇,醒来的我第一次问自己:如果我真的回不来,你会怎么样。”
“你说自己是最矫情的,那么我就是最粗心的,多少年的时间,直到常人说的岁月找上我,我才知道后怕的滋味。难道在这之前,我竟然是无所谓的么?我竟然能轻易对待别人的痛苦,就好像这些都不值得不应该么?那我就真成了天字第一号的混蛋了。”
林砧将手指蜷缩又伸张,转移自己的注意力,就像他现在一专注就要怎么了。
“但是我从没说过我是不是天生就缺少这种东西?我说不出来,不知道怎么讲,只好学你的样子,将你对我的好再赠给你。”
“你不必追,更不必觉得追不上。你早就追上了,只是我太差,就算当老师也不知道给学生一个奖励,就算是朋友也不知道和对方打一声招呼。”
林砧终于垂下眉眼,无奈一笑:“江匪浅,是我不及你。”
这话在江匪浅的脑海中轰然炸响,将他炸了个茫然无措,那双从来凝定的眼睛忽然茫然了,像是雨天草地里的烟雾气,飞扬开来。
风在树叶中游走,像是徘徊不定的灵魂在人间窥探着。但是江匪浅和林砧周围却冒出强烈的气场,将这灵魂一般的风打散了。
“希声,你再,你再说一次?”江匪浅不确定地对林砧道。
后者走近,按住江匪浅的肩膀:“听到我不如你,你很高兴啊。”
“不是”江匪浅嗫嚅。
“当然不是,”林砧笑了,道,“但是至少在对人方面,我不如你,我对自己远不如你对我好。以后这些问题上,还要向你请教。”
江匪浅露出一个笑容,但是嘴角却在抽搐,似乎是忍不住的情绪牵动了他的肌肉,让他无法自己。
“风铃声。”林砧张望着。
江匪浅也听到了,铃声清脆,穿过树林,带着风的呓语。“是行香铃,它还在屋外挂着呢。”听到这铃铛声,江匪浅恍惚了一下,仿佛现在回到家中,就能见到师父和君父。
但是斯人已去。
就像是知道在想什么,林砧道:“你这房子太久没有烟火气了,不好,我们进去住上一段时间,这房子才会活过来。”
想要说什么,但是却说不出。江匪浅狠狠一眨眼,唯恐是梦中,但是眼前人物,此情此景,千真万确。
“好啊。”江匪浅答道。
偌大的房子,若干年没有人居住,却是干净的,仿佛时时有人拂拭。林砧啧啧称奇:“了不得,了不得!我听说东方的道人有一种叫做避水诀的法术,默念这个法诀,身上就不会被水沾湿。老神师是不是给这个地方念了避尘诀?”
“当然不是。”江匪浅笑了,但是他也解释不清楚为什么这里一干二净。
林砧托着下巴想了半天:“难不成是因为他们知道你会回来住,所以特地让什么山妖精怪给打扫了?”
江匪浅很正经地道:“第一,他们已经走了;第二,山妖精怪不负责打扫卫生;第三,他们绝不知道我会回来;第四,山妖精怪如果为我做事,我岂不是成了山大王了?”
林砧显然只听见最后一点,高兴地道:“山大王有什么不好?啸聚山林,很爽快的呀。”
江匪浅哭笑不得:“我暂且没这打算,你倒是可以一试。”
林砧来了精神,跳到一张椅子上,腿往桌子上一翘,大喊:“哪个不要命的,速速上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