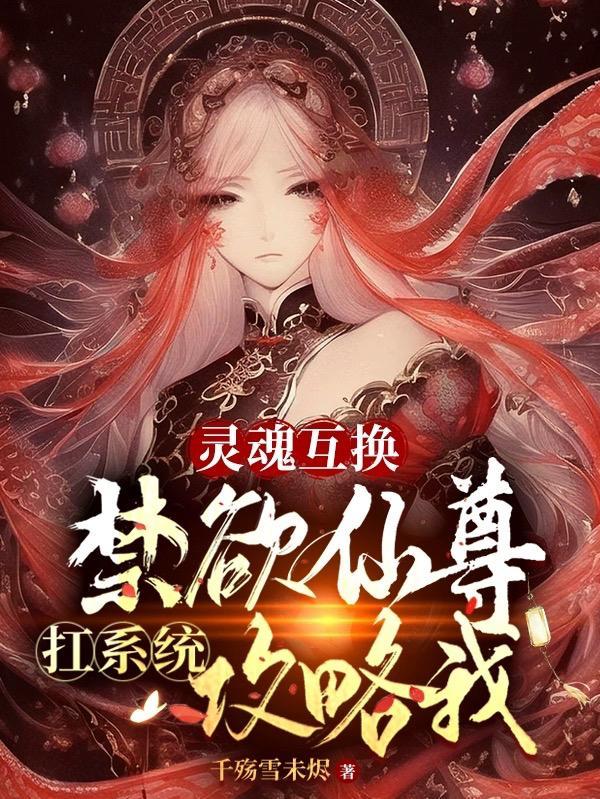大文学>死遁后我靠无情道飞升了 > 第129章(第1页)
第129章(第1页)
池应淮说着不禁摇了摇头。
温清川静静地看着桌上的茶杯,淡淡地开口,“然后呢?”
“到这里街坊邻居还只是认为他们一家是夜里出来,不喜和人交谈沟通,这倒也没什么,住在淮江的大多还是平民百姓,那些达官贵人的事他们掺和不进去,也不想掺和。但一年前的一个夜里,有个打更人从这薛家门口路过,刚靠近大门便被一阵阴风吹开,原先在夜里欢笑嬉笑的人家,宅院里全是齐刷刷的白绫,和坐在正中央身着红色嫁衣的女人,而她脚下确实满地的白骨。据说后来衙门来人,掀开了那新娘的头盖后发现头盖下也是一具白骨。”
“如果真如他们所言,那之前夜里嬉笑的声音便都是假的,薛家早在几年前便死了,所以才未曾有人见过他们出入府邸。当时衙门确实是想查此事,但无论他们将白骨搬出去多少次,就算是烧了扔了埋了,当天夜里还会出现在薛家的宅院之中,紧接着发现这事的打更一家便在一夜之间全部暴毙,原先想查的人此时也没有了胆子再查下去。”
“这件事最后还是落到了神域手中,神域办事向来是不允许平民百姓插手的,我在神域也只翻到了潦草的记录,好像只是一个魔族意外套出鸠千夜酿成的祸端,后来薛家被贴了封条,周围的百姓也因为害怕纷纷搬走,一时之间也没人再敢大着胆子不怕死地半夜去查看那邪祟是不是真的被祛除了。”
“倒是个诡异的事情,白日我也去打探了一番,和你打探到的一样,只是再谈起后来的事情大家倒是纷纷躲避不肯多说。在这茶楼的对面,有个没烧干净的纸钱堆。我去问了问当地的叫花子,听闻是茶楼对面的女儿前些日子出嫁,因为他们是后来搬入的,并不清楚之前薛家的事情,无意之间载着新娘子的花轿路过了薛家,等到了新郎家催促新娘下轿子时却迟迟等不到新娘的动作,媒婆上前掀开帘子后,发现轿子内只有薛家中央的那具白骨,而新娘却不见了踪影。”温清川淡淡地说道。
“而之后更是离奇了起来,凡是出嫁的新娘无论走的是那条路,最后都会路过薛家,再接着发生和先前异样的事情,新娘被换成了一具白骨,而抬着花轿的人却什么事情都没有,问起之前走过哪些路时,他们都是支支吾吾什么都想不起来,像是无端失去了先前的记忆,却在看到花轿里的白骨时,惊坐在地上无一例外地都说着曾在路上恍惚间看到了薛家大敞的大门。”
“也有人想去通知神域的人来插手,但凡是动了这个心思的人,最后都莫名在夜里暴毙身亡,一开始大家还怀疑凶手或是魔族藏在他们之中,怕事情败露才将想要传出消息的人呢杀掉,但很快人们发现了不对劲,就算不告知家人朋友,也会被无端杀死,因为有个又瞎又聋还不会说话写字的人的女儿也遭遇了不测,在当天夜里,这个男人也死在了陋舍之中。”
“之后便没有再动去告密的心思,淮江依然接待着客人,所有人都成了那魔族的同谋。”他将茶杯放在桌子上,抬眼看向池应淮,“负责这件事的,是神域的谁?”
池应淮眼中一暗,沉声道,“花家。”
“那便好办了。”温清川笑着说道。
池应淮不解地看向他,“什么意思?”
“既然花家插手,那便证明此事并非什么鬼魅作怪,只是人或魔或妖所谓,怕是根本不懂什么看破人心的术法,我们接下来也轻松些。”温清川说着便要起身,被池应淮猛地抓住了手腕。
“你想要做什么?”池应淮蹙眉问道。
温清川静静地看了他一眼,轻笑一声,“自然是假扮新娘,打入敌人内部,这还是你先前教我的话术,不是吗?”
池应淮手上用了些力气,似是不安地说道,“谁来假扮新娘?”
温清川莞尔一笑,好看的眉眼看不出一丝情绪,说出话无情至极偏偏声音温和像是在安抚着人的情绪。
“我来扮。”
默声
“听说了没,那河边哑婆的闺女今天就要出嫁了!”
“哑婆家的闺女前阵子茶楼对面绸缎铺家都出了那种邪门的事了,她家怎么还敢让闺女出嫁,哑婆平日里不是最疼她家那闺女了吗,成日当个宝似的,怎么这会上赶着让亲闺女送命去?”
“啧,这事是哑丫头决定的!”
“哑丫头?!”
“对!前些日子不是有位贵客前到官家那做客,你说好巧不巧那日他正好走到河边正好看到河边洗衣服的哑丫头。你也知道哑丫头人长得水灵,因为不会说话性子乖张温和,谁看了不心里软软的。那贵客在外面吃惯了山珍海味,一见到哑丫头这道素菜当即就走不动路,说什么都要娶哑丫头走。”
“官家那也没拦一拦?”
“嗐,官家那可是千般万般阻拦,明里暗里说这里风水不好,让那贵客赶紧回原地方去节礼。但你知道哑婆那个身子,常年累积下来早就空了底子,现在全靠哑丫头平日里卖卖刺绣得的三瓜俩枣买的药材吊着命,哪里再经得起折腾?要我说那贵客也是个实在人,是真的看上哑丫头了,当时就请来了名医给哑婆治病,但再金贵的药材进了哑婆体内也都跟烟一样,转眼就没了。那阵子哑丫头出来卖刺绣时眼睛都是红肿的,面色也憔悴许多。”
“那模样别说是贵客,就是我看了都恨不得跟阎王爷要人去。那贵客见状别说走了,直接命人在哑丫头家旁边搭了个小房子,在那里住了下来,说什么都要赶在哑婆去世前将哑丫头娶回家来,为此还特地请了神域的仙人来作法呢!”